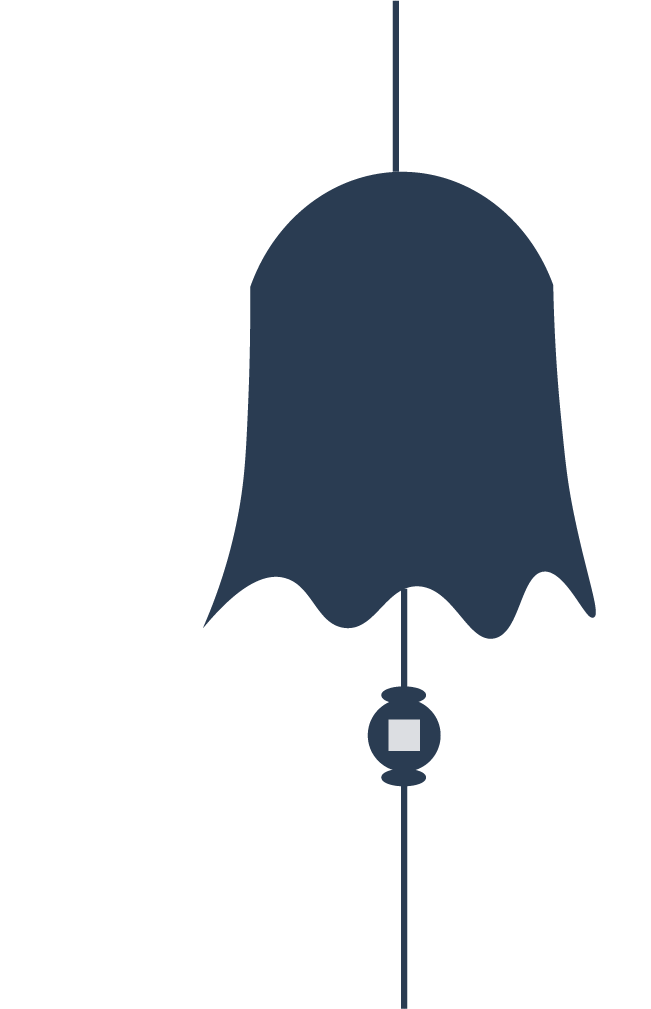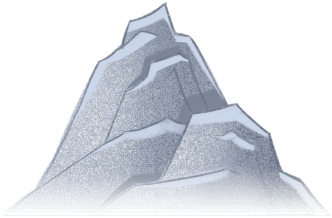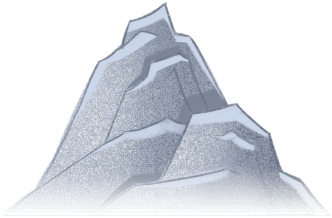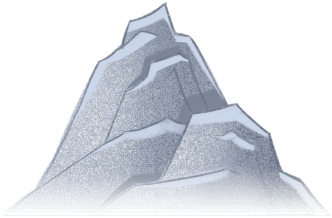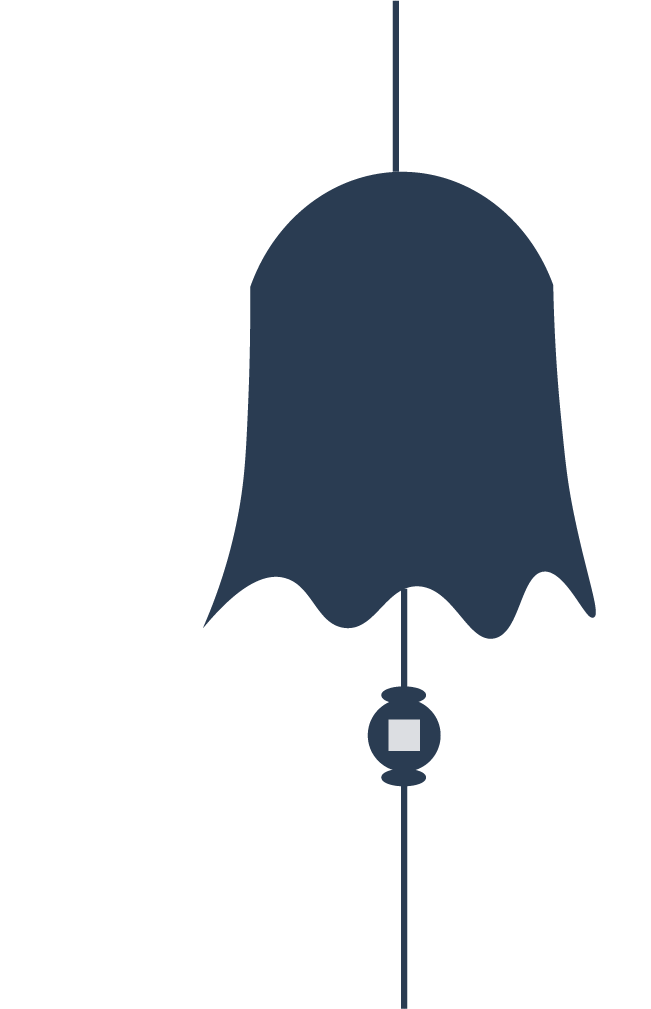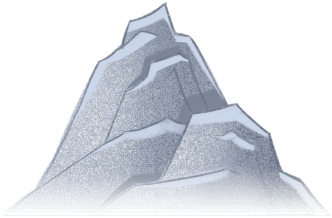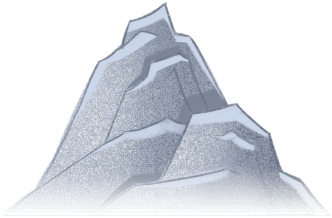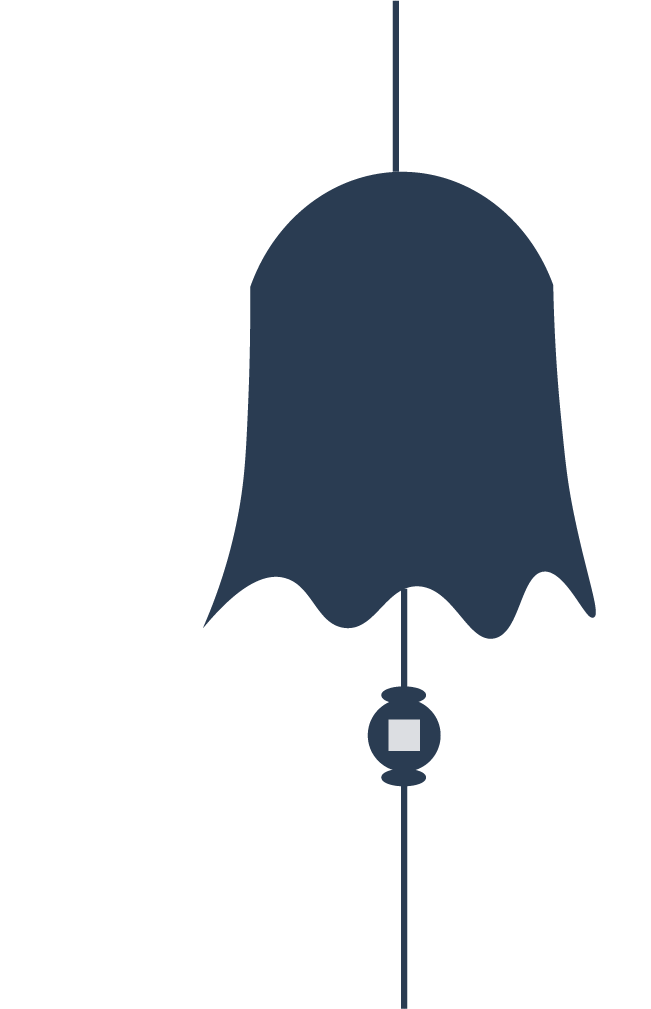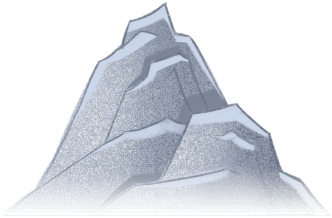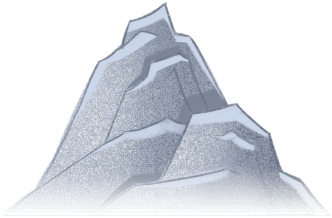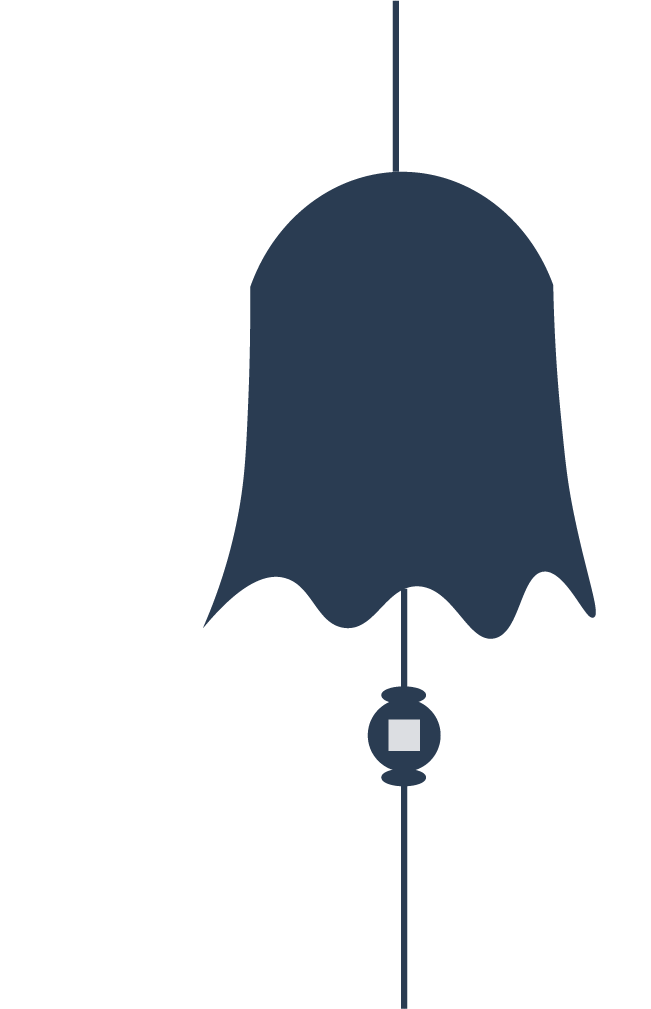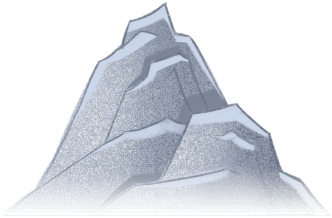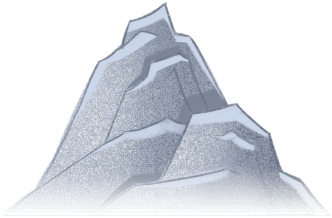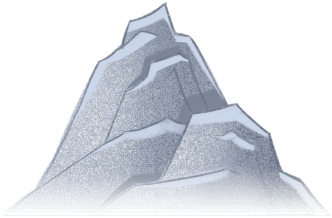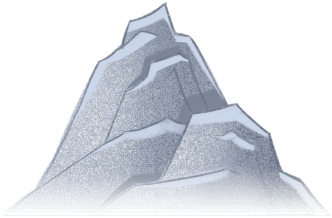傅强|游记|跨越时间的瀚海找寻你
- wang
- 2023-09-27
- 生活笔记
- 81浏览
- 0评论
“泱泱中华,如日之升,如月之恒。”仰望良渚文明的古迹,圆璧、方琮携着神人兽面纹,我不禁为其久久驻足。先民埋下的文明的种子终于重见天日,良渚博物馆如一叶小舟满载我们穿越历史长河,与良渚先祖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邂逅。
初一进馆,我便被琳琅满目的玉器与巧夺天工的陶器簇拥。面对纪念墙时,有那么一刹那,我仿佛是千年前的奢靡贵族,把玩着进献来的宝玉;我又似乎是满身脏泥的工匠,用我的双手给予陶泥温度。累土的地坝蓄起了千年中华的底蕴,石磨的犁具耕开了华夏圣地的沃壤,良渚文化在一锄一犁,一针一线中诞生、成熟并在千年后再焕辉煌。
停留片刻后,我步入展厅,耳机里响起讲解员的声音——“这个内圆外方的玉琮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……”它不似常见的宝玉那般翠绿、通透,更像大理石,纹理清晰,浓实的白色里揉开一抹黑,好像天然的水墨画。讲解员解释道:“这是玉石时间久了的受沁,古玉原来是很透的。”它就静静地站在那里,隔着玻璃与我们对视。我的脸不自觉贴上玻璃柜,我的手贪婪地伸向那玉琮,渴望抚摸它岁月摩挲留下的粗糙玉面,然而,“一毫米的玉面可雕五道纹,互不重叠”一行小字闯入了我的视线。神纹线条深浅不一,却十分工整,其纵横交错组成的质朴几何图形透露着无上的庄严。这是何等的出神入化!那一方玉琮上的细腻纹路挑拨着我的心弦,美得惊心动魄。我以为,既然是史前,那必然是稚嫩青涩的,至少也是做工粗糙,经不起细细琢磨。可这一神人兽面纹却颠覆了我的认知,他们的工具或许简陋,但他们的匠心不可否认,其技术乃至现在都值得借鉴。
道别一厅,我走入了二展厅,目光不知往哪儿放。叫不出名字的玉器,不明用途的陶器,莫名令我有些无措。稍一不留神,便与队伍散开了。我只管走,无目的地晃荡,最终停在了一个出现在博物馆有些突兀的展品——一具女性骸骨。
“这是良渚时期的女性骸骨,她的身高是158……”
是现在女生的平均身高。我注视着那具骸骨,眯上眼睛端详了好半天,期望着看出点什么名堂来。大概是岁月的敲打,她灰白的头骨并不完整,四肢也有一些缺口,左脚又被展柜内的沙土掩上了。但似乎,我们有的特征她也都有,五指、手臂、双腿甚至体型也并无差异。乍一看是不见有多少亮点的,猜是因为我们本就同根同源,她与我们便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相像
我摇摇头走出展厅,为她的普通而惋惜。一到门槛,我顿住了。仿佛一道响雷忽的把我劈醒——,这是一具4000年以前女性的骸骨,我们竟何其相似!她确实别无特别,但她来自千年前,千年的光阴有能力夷平山脉,却不能抹去她的面容,留下了她对我们的赠礼。我们的宗法血缘已是淡到无法计量,可我们却拥有着相同的骨骼、相当的体型、相似的面容,我们胜似亲人。没有文书能以原本存续4000年,而她做到了。她跨越时间的瀚海找寻着她的子孙,赐予我们同样的面容,慈母般爱抚着我们。我看着她被复原的面容,她的骨节,我仍觉得我是她的孩子 。
既来此良渚博物馆,又何有不览遗址一说?短暂休整后,我们乘上观光车,行车在一丛丛摇曳的芦苇荡中穿行,远处的草屋将城市的喧闹拒之门外,洒下的阳光铺满旷野,将空气都渲染得柔和。不知多久,在芦苇丛的庇护下,我们穿越了都市的屏障,闯入了良渚的桃源。行车在一条石阶前停下,我们最终踏上了朝圣之路。脚踏王殿遗址,眼观古城无垠,千年前,这里金碧辉煌,千年前,这里歌舞升平,千年前,这里河清海晏。然而,所有曾经的繁华都湮于烟尘,我们本无缘相见,可我们却作为唯一的文明古国香火不灭。是有一群人,持铁铲填平了我们与良渚的沟壑,用双手搬开了封印这一国度的巨石,拿尺规度量出千年的长度,以热情与使命为浆,跨越时间的瀚海找寻她。考古人的匠心点亮了沉寂千年的良渚文明,回应着远古的呼唤,向世人揭开了良渚文明的帷幕。我们能以灿烂五千年文化为傲,是因为有人青灯在心独守宝窟,是因为有人黄沙满面与土地对话。是他们,又不只是他们。只有华夏子孙认同良渚文化为祖先文化,只有人们昂首挺胸充盈着文化自信,良渚乃至所有文化遗产才真正活了第二世,迎来第二春。
参观的时间不长,我却恍惚间开启了一场时间旅行。站在古城的遗址,看这一片疏疏落落的土坑,我走上朝圣之路。城池会磨损,玉器会受沁,文物会磨损消殆,但文明却在稳定而长久地赓续,在传承不息中铭刻永恒。
文明的传承,大概就是博物馆的意义,亦是渺小人类文明的伟大。
声明
1.本文的内容、编辑、排版由作者一力完成,文责自负
2. 文章:傅强
3. 图片:傅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