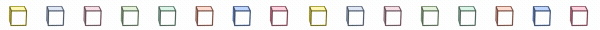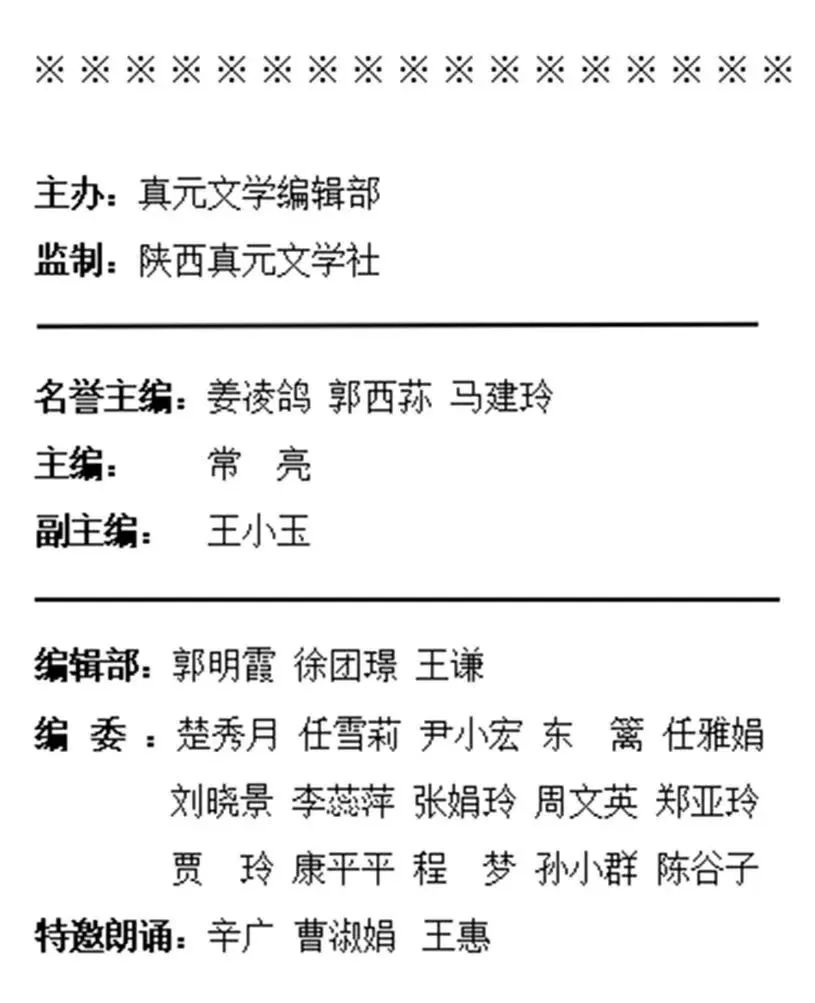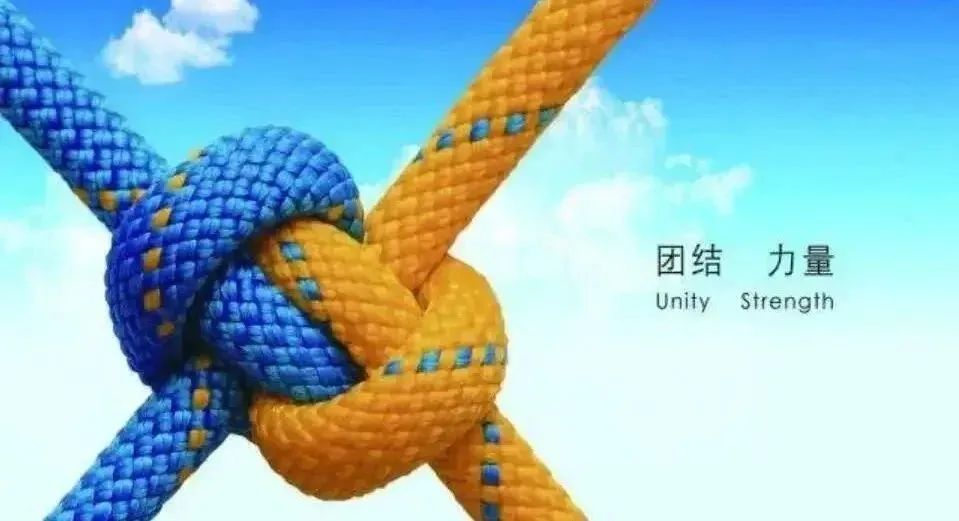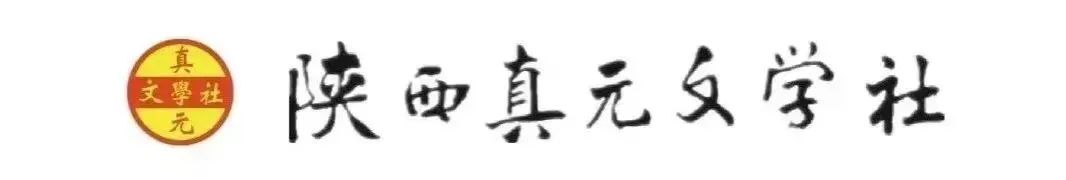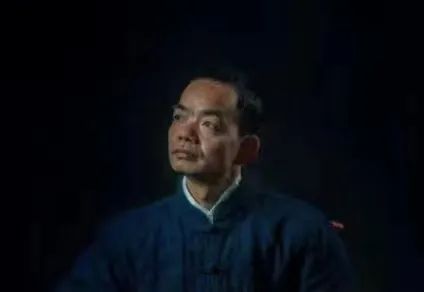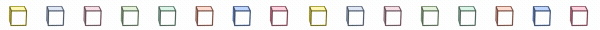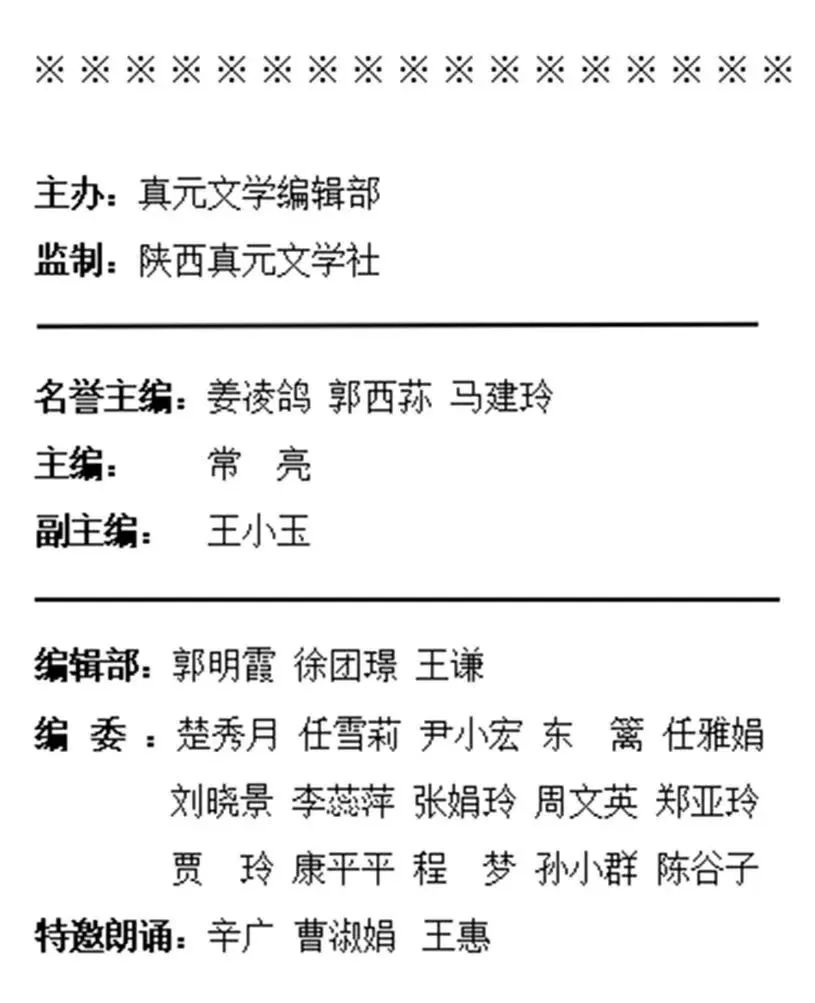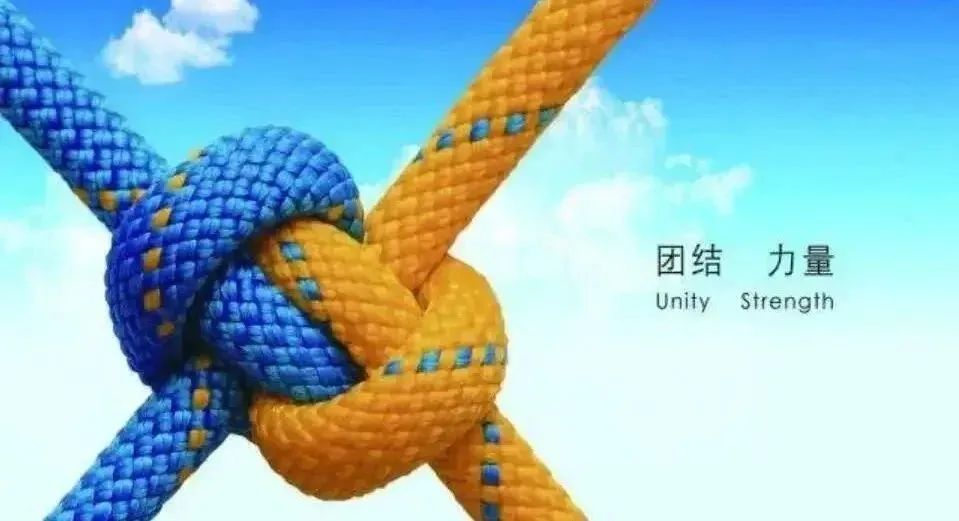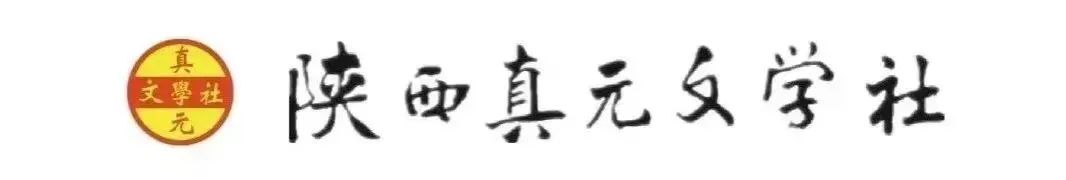

雅乐吴题
——终南山游记
文/董宏永
终南者亦曰,周山、南山。秦岭主脉,雄峙于长安之南,绵延数百里,钟灵毓秀,奇峻遂远。闻传伊喜善观星象,楚怀王时任函谷令,结草为楼,登之以观天象。一日,见紫气东来,一青牛老者身披五彩云衣,西游至函谷,遂接入楼观,闻道德真经五千言,始有道教。 终南神秀,华夏龙脉,自上古之时起,便多有隐者以修仙道,应接山水之灵,天地之气,日月之华。 岁在丁酉四月初夏,终南鲜峪草堂,京都雅乐府吴题,轩辕陵祭祖礼成,携友人锦田、久歌 、乐云,赴终南览圣,至以电布,遂与少陵制埙师田懿驱车会之。
初见甚异,惊若天人,一行四人匀汉服着身,言行举止,儒雅有致。不似吾辈之,放浪形骇以为常,言语随口欠走心。吴题善乐,容颜俊朗而和气外露。锦田善度之以谋而正气凛然。久歌善礼而通文。乐云善舞,面慈而喜佛乐道。是日,虽层云浮顶,但雨碎而风柔,山高云底,峰峦隐幻,林木阴翳,泉清而石新。更异山花掩映,万物清而绝尘,气馨而神爽。 临泉石上,吴题埙乐渐起,苍远浑厚,抑或忧郁而缠绵,仿佛穿越亘古,直扺洪荒,神驰旷远。锦田盘膝而坐,闭目观心,静若止水。乐云舞起翩跹,漫妙悠然,晃若天仙。是以山水映人,人应山水,若梦若幻,陶然于青山绿水之间,忘却闹市纷繁,于重林幽壑处,绝出红尘外,迷醉不思归。久歌畅而赋怀“凭生问道烟雨处,不若归去此山中”。
大凡人之有缘,于冥冥之中皆有注定。 乐云喜佛,或念力所至,邂逅于终南隐僧宽涌法师,众人心奇于隐者居境,随往拜之以问道。法师居于山之腰,凿石窟以奉佛,建廊轩以参禅。蹊径隐于密林之间,崎岖峻险,一众相扶而上,气嘘不以。至上眼界顿开,举目薄黛青山烟雨外,近看佛堂禅舍草木中。虽不至山顶,却空悬世外,似若仙境。 宽涌法师,俗名泉永,年少尚武,好勇斗狠,不信神邪。无意间顿悟以归佛门,云游四方以求真道。后拜高师而隐于山野,至今二十年矣。 法师云,凡真修者,修正法门,修正心,修自我,修纯善。去本我,去超我,去七情六欲,去凡尘杂念,不垢不净,不尘不染。得解脱以得大自在而成仙道。 然修行之途异常艰辛。凡大成者,皆受常人所不能受,历常人之不能历。几世方得正果。稍存凡心杂念,或法不正皆可前修尽毁。是以真修者需存挚真,挚爱,挚纯,挚善,挚坚,挚毅。加之佛性慧根,机缘巧合,而能得成者亦凤毛麟角,非常人可遇之。言其前世乃一修者,今世续修。 法师善道,布善厨。借法师炉灶食材,做素面斋之众人,虽简陋,但佐以山涧清泉,更得心于法师佛性,亦清馨爽口,芬芳自然,众人皆赞。
斋毕,吴题尺八奏乐,法师焚香诵经。佛音天簌,不悲不喜,亦空亦色,素净通明。禅舍外轻风细雨,山空林静,余音袅袅。此时此地,放空自我以净涤心灵,超然出世以忘却烦忧。次日出山,临近峪口,路遇养蜂人,言其身后半崖有洞,隐一少年。众人甚异,欲探之。问路之远近,曰不远无径,入谷口五六十米,攀石而上。众遂往之,入谷攀行百余米不见欲反,忽闻左后崖畔有声呼曰,此地无路欲意何往?众反而会之。少年约莫十六七岁,衣衫褴褛,面目清瘦。穴洞而居,洞半掩其口,深约六七米,只一床一灶。洞有台口十余平,少年垒石为田,填土植菜。问其何方人氏,原何隐于此,答曰川西,家生变故,出走至此,喜道遂隐此山四五年矣,问其生属曰二十过一。 问何以为生,此空山孤寂何以排忧。回,打工以赚米粮,植菜,指曰山有泉。众望之,山隙有水,滴若莹露,撮土为堰,弱水半洼。吴题锦田匀俯地口噙山泉尝之,曰清洌甘甜,沁脾入心。 
少年亦曰,山中有师,常去听禅,得只字片语,回洞打坐自悟,得心不少。闲时学笛以解优,虽初学甚爱,遂示一笛,吴题接之,信口一曲,清脆嘹亮响澈山谷,少年初闻惊异而后笑若莲花。曲终,众人欲辞,吴题悯其孤苦收为徒,互留信。众人退,布耳语少年,真有仙否?答有仙信否?笑若莲花…… 至此众人出山。布驱车送众人乘机反京,途中问曰,真有仙否?皆难以言明,曰信则有之,不信皆则无。又问信否?吴题曰,信与不信吾辈不知自有人知,然有佛有道,修者自修以布善道,自爱以泛爱众,善莫大焉。 嗟吁!神仙之事吾辈之人自难言明,然既已为人,自先为人道,不能人道,何以仙事。既为人若老不能敬,下不能教,友不以诚,言不立信,亦何以立人。既已为人,自常律己以宽人,尊重生命,珍爱生灵,敬畏自然,此生不求通达富贵,但求问心无愧。心安即自在,何去羡仙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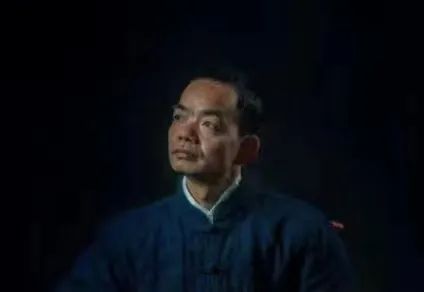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董宏永,长安少陵原人,农民,厨师。敬畏自然,敬老孝道。在红尘世界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。在简单的生活里追求一份精神寄托!喜爱阅读!喜爱文学,喜爱吹埙吹箫。陕西真元文学社会员,西安国学诗社会员。
本期责编 王小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