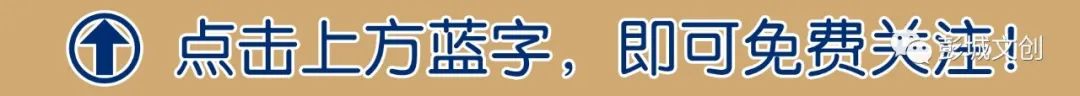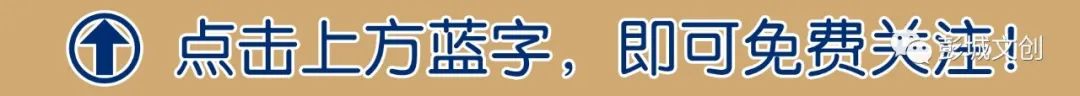云龙山游记
- wang
- 2024-01-24
- 生活笔记
- 72浏览
- 0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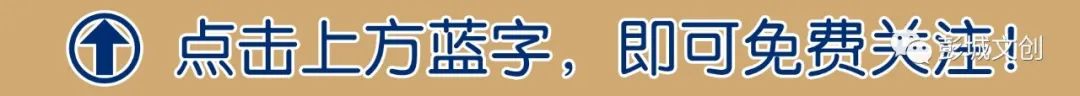
木心说,晴秋上午,随便走走,不一定要快乐。出去走走,锻炼,舒筋,活络,转换心情,肯定快乐啊,不懂得木心为什么要这么说。 前一阵子,秋风乍起时,想找朋友一起爬山,闻一闻放鹤亭前的桂花香,想想还是算了。 山上有桂飘香,尤喜放鹤亭小院内的老桂。亭前右边有成人腰粗的刺槐,春天来临的时候,雪白的洋槐花挂满枝头,整个山头洋溢着香香甜甜的槐花味。 放鹤亭独门独院,四周有廊,前后通透,后门长锁不开,绿树环绕,北侧有绿竹相拥。小院方方正正,座东朝西,小院不大,几个平方,方块石板从中间把它分开。金桂石榴,树靠着树,枝连着枝,绿叶压着绿叶,挤挤挨挨,逼仄幽深。桂树还揣着最后一点儿残香,弱弱的缭绕着。桂树蓬蓬,树冠很美,花香倾城,花貌平庸,四平八稳,叶片苍绿。有时候觉得,美丽是需要有合适的空间去舒展的,这树尤是。
进得门来,迎面靠墙的是一幅木制影壁墙,上绘《听泉图》,四周雕花,厚重沉稳,墙上悬挂着苏轼和张天骥的画像及其简介字画,南墙北墙边各放两把太师椅,两张书条。 放鹤亭内的这太师椅和书条有点小哈。想起小时候,我大姥姥家有一张很大书条。姥姥家的八仙桌子旁边,放着两把很气派的太师椅,时间虽然过去了很多年,仍记得那颜色黑红黝亮,桌子后面是一个长长的高高的大书条,通体雕花,两头上翘,右边一个青瓷大花瓶,里面插一把拂尘,还有那种暗黄色桑皮纸样的旧画卷。进的门来,常常见到个子小小的姥姥端坐在太师椅上,手持长长的白玉嘴烟袋锅,花白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,束在脑后,用黑色网纱裹成圆圆的发髻,一根银簪贯通别着。不上学的时候,母亲领着我回娘家,我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姥姥,抽着长烟袋,三寸金莲离地悬空,也不大说话,每每看着她威严不语的模样,我都吓得不敢乱说话。 季节还是那个季节,岁月还是那个岁月,却是物是人非,我的大姥姥早已驾鹤西游多年! 室外大树遮日避天,室内没有灯光,显得昏暗阴冷。有一七旬白发老翁,高高的个子,身穿白底暗格衬衫,精神矍铄,当天是他的生日,让我帮忙,说想在这儿拍几张照片,好给远在上海的朋友寄去。好吧,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,我也乐意为之。看了看室内太暗,只好到门口拍了几张,在亭子西南角那个苍劲有力的大大的寿字碑前,给老人多拍了几张,老人生日嘛,祝老人家生日快乐,又拍了壮观碑及饮鹤泉碑,老人笑吟吟的,他很快乐,我心里也愉悦。老人还想找点介绍苏东坡的宣传图片贴在信封上,给亲戚朋友寄去,这些宣传材料云龙山园林管理处应该有吧,短时间内哪儿寻去,老人最后没能如愿。 站在一亿年前的云龙山上,望着千余年前的苏轼和张山人推杯换盏,唱和作诗的生活遗址,以及放鹤亭门头那绿盈盈的苏轼手迹“放鹤亭”,看着周围的游人,感叹时间犹如白马过隙,人类何其渺小,短短百余年的人生,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粒尘埃而已。
云龙山,爬了N次。以前孩子小,工作忙,偶尔带孩子来玩,总是走马观花,快退休的时候,身体不舒服,爬山是为了恢复身体,锻炼体能,现在来爬山,纯粹是找乐,逍遥,消麽时间。 从张山人故址大门进入,左转,顺着长廊来到船厅正面。 眼前的船厅灰瓦飞檐,暗红木方格栏窗,曲廊倚楼,古色古香;拙朴而又厚重,有岁月沉淀的历史感。我从没有进去过,每次来都是铁将军把门。 这座船厅始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二年,由当时的徐州知府田庚所建。因其造型似船,故而被称为船厅。两层砖木结构,上面似船,下层是厅。登其上,如乘船腾空,飘然若飞,湖光山色尽收眼底,故又称船厅为“天上座”。据说,厅西面墙上有匾一块,上书“天上座”三个字,匾下有对联:春水船如天上坐,秋山人在画中行。 船亭地处僻静,常有文人闲客在此吟诗,赏景,闲坐,刷抖音。 四扇单开门,正门烫金对联为书法家王冰石老先生所书: 对联中有些字不认识,回家后专门请教了一位诗友才读得通。 厅三面长廊,颇有江南园林之趣。西侧和长廊相连,廊外有桂,北侧青竹摇曳,秋风穿过,凉意顿生,东北侧下坡杂树横生,错杂相拥,木本,草本,藤本,常绿的,落叶的,带刺的,开花的,挂果的,或缠或立,你扯着我我拽着你,为一点有效的养分和天日相互争夺。
船厅座北朝南,正面有台阶,左面为碑廊,右为放鹤亭。 碑廊里的字碑,经过日晒雨淋北风吹,有些字迹很难辨认,现存有元明清时期大小碑碣62块,大书法家董其昌、褚遂良、乾隆等著名人物在这儿留下的墨宝,行书、草书、隶书还有篆书等书体,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! 船厅东墙,有一个铁门紧闭的小室一间,门上铁狮衔环,从门里引出两道铁轨,距离小室一米多处,有石窝,一个黑黝黝而且锈迹斑斑的轴承卧在里边,轴承上有凹槽,向下的铁轨有半米之宽,一直延伸到山下盘山公路边。有游人猜它大概二三百米。从坡底往上看,仰角大概40℃左右。 拾级而下,这儿游人很少,石径迂回曲折,悠长僻静,三叉树下,竹影清丽,有石桌石凳,斑驳陆离的树影落在石桌石凳上,可供游人歇脚。坡边石缝里,八角金盘葱葱郁郁,这种绿植最喜欢在阴影里生存,开着洁白小巧的云一样的花朵,与宽厚的绿叶依偎在一起,周围沿阶草青翠欲滴,南天竹顶着串串鲜红。 台阶南侧有高墙与寺庙隔开,中间是铁轨,北侧与山西会馆一墙之隔,墙边荒草丛生,杂树荆棘混长。 沿铁轨往下看,轨道中心铺着石条,间隔处用混凝土和碎石子填满,起到加固的作用。轨道北侧紧贴山西会馆的南墙。石阶与铁轨之间,有高大的侧柏,褚桃树,还有一棵老石榴。 从上而下,顺着台阶,来到山下公路边。扫地的老伯打招呼说,累不累,台阶可有219个呐。我问他:“这铁轨是干嘛用的?”老伯说:“是当年重修船厅时往上运送建筑材料的。” 联想到前两年,和一群文友去爬泰山,泰山西坡也有两条铁轨。我们从西坡小路上山,顺着两条铁轨往上爬,山路很陡,我和一位文友手拉手踩着石缝,走着S型,抓着小灌木,抱着路边树,艰难的往上爬。有的文友直接顺着铁轨往上爬,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泰山海拔232米,西坡的铁轨从山脚到山顶,距离老长,爬的费劲,文友说,仰角得有45℃,有文友说,差不多。好不容易爬上去,铁轨的尽头就是庙宇。喘息间,有文友问道,这铁轨是什么时候修建的,它是干什么用的,一行人都摇头。同行的一位文学造诣颇深的师长让我写一下这个铁轨,目前市里还没有人写。老师布置了作业后,没多长时间我的脚被撞了,三耽误两不耽误,想写的心气也没了。
很卷的年代,没有高大上的理想和追求了,忙的时候就忙,闲的时候就闲着,有时养养花看看书,看看植物志,查查不认识的植物,读读宋词元曲,翻翻诗词里搞不懂的典故,也挺好。 比如说,前几天看到苏轼写的《游张山人园》,诗中提到园中养的一种叫“锦被堆”的花儿,花名好陌生,这“锦被堆”到底是个什么梗。“壁间一轴烟萝子,盆里千枝锦被堆。”当年张天骥的房子前,有一个大园子,园子里种着的叫做“锦被堆”的花儿,这花俗名粉团花,花枝细长,花朵是粉红色或微黄色。 想想当年山人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,他爱好诗书、花木和音乐,父亲嗜道,母亲礼佛,平时抄抄经书。没有稼穑之苦,不为稻梁发愁,是个殷实之家。在云龙山西麓黄茅岗,筑有草堂,房前有花园,养花种草架个鸟,还养一对仙鹤玩玩,建了放鹤亭,又垒了招鹤亭,早上放出仙鹤,黄昏,一声声清脆的口哨里,晚归的仙鹤呼啦啦飞回身边,哼着招鶴歌,喝着小酒,真是逍遥自在。有空再和苏轼等友人三五一群,温酒小酌,推杯问盏唱和诗文,园外还有童仆为其养马。 山人不喜做官,在云龙山脚下隐居。巧遇到的这位苏太守,乃性情中人,飘逸豪放,做事不拘一格,和山人三观相同,志趣相投,关系挺铁。(苏东坡在朝廷上四面树敌,在他历经命悬一线的乌台诗案后被贬谪到了黄州后,一般人躲都来不及,但张山人还去黄州看他,可见是真朋友。)闲暇时他们一起吆五喝六,划拳猜掌,喝得醉眼迷离,不信你找找,他在徐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写下的诗词文章,多是宴游、唱和的多,工作上,政务上的事,写的真是不多。下面这首诗就是个例子: 没说错吧,是不是这样,酒后的苏轼,手舞足蹈,醉态毕现,连路过的百姓都看了他的笑话。 “ 满丘乱石也平平,一醉坡仙便著名。”一块平展的石头,普通普通,因为苏东坡这醉酒一躺,从此声名大振,云龙山上又多了一景——“东坡石床”。 苏轼和张山人志趣相投,很谈得来,他写著名的《放鹤亭记》,写《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》,写《游张山人园》,写山人的花和鸟。 千余年来,天下隐士何其多,历代太守也不少,诸如张山人和苏徐州这样相互欣赏相互唱和,友情深厚流芳百世的人还真不多见,他们也是相互成就吧。也为今天的云龙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景观。
游园诗中,这“壁间一轴烟萝子”好解释,是说山人幽居的房间悬挂着的一位学仙得道者的画像, 但这盆里养的锦被堆是什么花呢? 要知道,一种花的叫法何其多,且古今叫法也不同,查阅一下资料,说是锦被堆,既可说是蔷薇花的俗名;又可指花名,叫粉团儿;还说是瑞香花。 那意思是锦被堆既可指蔷薇花,因为有粉色,有黄色,也可以说是瑞香花喽。 蔷薇花,香料植物。有刺灌木,有时蔓状或攀援状;叶互生,奇数羽状复叶;托叶与叶柄合生;花单生或排成平房花序或圆锥花序;花瓣花单生或排成平房花序或圆锥花序;五个花瓣,有时重瓣,花色有粉,红,紫,白,黄等色,有诗人说它“貌特媚,嫣红古白,嫋嫋含笑”。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花儿。 瑞香花是一种常绿直立灌木,高约2米,枝较粗壮,常二歧分枝,小枝无毛,近圆柱形。叶互生,纸质,呈长圆形或倒卵状叶互生,花无毛,外面淡紫色,内面呈肉红色,数朵至12朵组成顶生头状花序;苞片为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,花萼无毛,有香气。我虽然养了不少花,但没养过瑞香,据说瑞香花有毒,毒到花下寸草不生。瑞香生活在温暖的南方,当年是一位在山里睡懒觉的和尚发现的,后来,小日子的诗人也喜欢,于是被远涉重洋带回了东瀛。 虽说一个是和尚,一个是隐士,都不是寻常人,被他们喜欢倒也是瑞香的荣幸,但是,张山人花园里的这株花应该不是它。 和山人同时代的诗人宋祁在《益都方物略记.锦被堆》里记载过:"俗谓蔷薇为锦被堆花。" 诗人刘子犟也曾说:"锦被堆,一名粉团儿。花如月桂而小,粉红色,或微黄色。叶亦相类,而有刺,枝柯纤长丈餘,往往作架承之。" 瑞香花无刺,既然有刺,枝柯又纤长丈余,花色有粉色有黄色,说明当年张天骥养的花儿是蔷薇花没错。 搞清楚了彼此,心中暗自窃喜,也很有成就感,特记之留念。
 王永平,网名“凤凰涅槃”,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从八十年代起,陆续在县级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,期间偶有获奖。作品选入徐州市作家作品选《千钟一饮》。
王永平,网名“凤凰涅槃”,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从八十年代起,陆续在县级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,期间偶有获奖。作品选入徐州市作家作品选《千钟一饮》。

本站文章除注明转载/出处外,均为本站原创或翻译。若要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,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共创和谐网络环境。
转载请注明 : 文章转载自 » 纵马网 » 生活笔记 » 云龙山游记